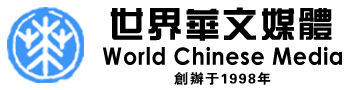顽强的生命之火 –深切悼念王唯真
作者:陈 健

陈 健
王唯真的生命之火,在几度明灭之后,终于熄灭了。
他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惊叹。多少次了,觉着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却出奇般地又回到亲朋好友之间。他患过癌症,两次开刀;他曾患肺结核、心脑血管病等,多次住院治疗。由于从热带潮湿的东南亚来到风沙干旱的黄土高原延安,气候水土不适应,他终生患鼻炎,做了多次鼻甲切除术。2003年他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我去他家看望。他躺在医用起落病床上,腿被绷带固定着,牵引在床尾栏杆上不能动弹。本来就瘦弱的他,越显瘦弱了。我回家对老伴周原说,老王这回可能真的站不起来了。时隔月余,他和夫人陈萍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一时无言表达心中的惊愕,立马掩饰住,连声称赞:“奇迹!奇迹!”
王唯真住在三里河,在皇亭子过组织生活,八十几岁的人,往返于两地之间,经常是乘公交车或步行。他家中的摆设几乎和北京市一般居民差不多,没有一样奢侈品。他搬到三里河住时,房子是旧的,大门坏了,总社派人帮助钉了一块铁皮,就凑合了。他从来没有装修过房子,夫妻俩连小时工也不用,一切家务琐事都由自己打理。王唯真行政十一级,陈萍也是离休的老干部,没有什么额外负担,生活应该比较宽裕。他们如此艰苦朴素,我原以为是老同志贯有的老传统,后来,我了解了王唯真和王氏家族的历史以后,才悟出这是出于他的信仰。
他这次突然犯病,就近住到铁路总医院,我去看他的时候,应该是病危时刻,但也不像先我去探望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已经昏迷。他认出了我。陈萍说,上午社长田聪明来看过,嘱咐医务人员说,他是爱国华侨,要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医生给他注射了贵重的针剂,现在有了出奇的效果。我弯腰伏在他耳边说:“等你病情稳定回到家里,我去和你聊天。”根据以往的经验,陈萍以为他的病情有了转机,直觉却告诉我:这是回光返照。回来的路上,我哭了。
我和王唯真的相识相交,是在黑云压顶、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是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是总社代理社长。我能忍受丈夫周原被打成右派后物质条件的匮乏,却忍受不了批斗挨骂、限制自由、强行劳动和无处不在的精神虐杀。一天夜里,我冲出分社大门,像囚犯越狱、像一头受伤的牛窜出牛棚,逃到北京,闯进王唯真的办公室呼救:“王社长,你要救我……”
我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被迫走向与一个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暴政挑战的道路,几行简单的文字,说不透我以死相拼的愤慨和胆量。
我和周原当时都是河南分社的记者,文化大革命本来与我无关,却与周原有关。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劳改中差点饿死。几年后回到分社,第一篇报道就是新乡县刘庄的支部书记史来贺,这个长篇通讯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发了社论;第二篇是通讯《管得宽》,我定好题目采访了一半,因客观原因交给周原,稍后总社来的冯健对此很有兴趣,由他俩共同完成;第三篇就是周原和穆青、冯健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三篇东西当时在河南、在全国都引起较大的反响,特别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了轰动。
但这些成绩并没有使分社社长朱波对周原手软。文革一开始,他以为一九五七年又来了,首先把周原和我揪了出来。不久运动转了向,造反派又把朱波揪了出来。我们原以为可以松口气解放了。不然,分社造反派头头刘健生、一个历次政治运动的打手,一个运动痞子,他一手揪住朱波,一手揪住我们。他手下有一名得力干将林某,是到分社不久的大学生,身强力壮,在院里一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感到恐怖。他一巴掌打到周原脸上,使周原踉踉跄跄站立不住。他们知道周原是烈士的后代,多位长辈死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却命令他站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罪名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以上的迫害还属共性,下边的个例却把周原推向绝境。《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被兰考地区的反对派宣判为“大毒草”,他们成立了揪斗三名作者的战斗队,一批批红卫兵来分社揪斗周原。关于这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动全国的通讯的采写情况,当时是由作者之一的副社长穆青负责口头向外介绍,文字介绍则由作者之一的冯健负责,周原倒落个清闲。现在一说是“大毒草”,铺天盖地的“罪名”压向周原。周原对兰考的反对派说:“这篇通讯是三人合写的,有三人的署名。”他们说:“我们去北京找过他俩,他俩都说,这篇通讯主要是你采写的,他们不了解情况。”
为了配合兰考的斗争,刘建生、林某锣鼓喧天拉着周原游街示众。他们如此百般折磨周原,是他还有个“把柄”在他们手中攥着。周原1957年因为说实话写了三门峡的内参被划为右派后“秉性难改”,劳改时又说实话被定罪为“攻击三面红旗”,再次遭到比五七年更严酷的批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举刀砍断了三个手指头,写了“断指血书”,这在当时叫反党。刘建生、林某把周原拉到大街上,强制他举起断指的那条手臂,向围观的群众嚷叫:“老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了大毒草焦裕禄。”我冒死跟在离周原不远的一群人中,怕他被乱棍打死。游街示众后,刘、林不让家人知道,又把周原送到一个“牛鬼蛇神”集中的地方,残酷批斗、强制劳动。在这之前,他们还把周原的母亲——一位年迈体衰的烈士的妻子赶出分社。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用文字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我必须争得人身自由,才能寻找我的家人,保护我的孩子不流落街头。但我没有人身自由。我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被强制性地扫大街、擦洗厕所,随时随地被抄家、批斗、训斥,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总社有报道任务下达时,由女造反派头头押解我下去采访,稿子写好交给她后继续劳改。我唯一的“罪名”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
一天深夜,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院子里最显眼的地方,大意是警告刘健生、林某:你们要是跟踪我、抓捕我、限制我人身自由,一切后果由你俩负责,我现在要去北京告你们。
分社一共几十人,办公室和宿舍在一个院子里,进出口只有一扇大门。看管大门的张大爷住一间平房与大门紧挨着,晚上没有人出入时大门由他落锁。从1957年反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对周原和我都十分同情。我贴好大字报,一把推开张大爷的门,他和张大娘披衣坐起吓得直哆嗦。我说:“张大爷,快给我开大门,我要跑。”这正是一月底或二月初,最冷的时候。张大爷问:“兵荒马乱、天寒地冻的,你往哪里跑?”我说:“我去北京告他们。”求他快穿衣服给我开门。他因为又冷又惊,胳膊伸不到袖子里。我帮他穿衣时,想到我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就说:“刘、林如果逼你太甚,你就说我砸开你的门,在桌子上拿走钥匙……”张大爷打开大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又扭过头乞求他:“天亮时,请张大娘偷偷去我家看看三个孩子,叫他们不要怕,说妈妈三五天就回来。”张大爷猛推我一把:“快跑!”
分社离郑州火车站有五六站,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这时已经没有了。我一口气跑到车站大厅,在一个角落处瘫软下来。我的毛衣毛裤连着内衣因出汗湿透贴在皮肤上,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在发烧。那时,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要么是晚上,要么是早晨。我等到天亮爬上火车,天黑时在总社招待所门口因没有带任何证明不准住宿而蹲了一夜,在分社我已有几天几夜没有吃好、睡好。此时整整两天两夜不进茶水饭粒的我,来到王唯真的办公室时,已经难以支撑了。
以上这一切细写起来要很多文字。总之,我闯进了王唯真的办公室:“王社长,我是从河南分社偷跑出来的,已经没有了退路,你要救我。”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谈了我一家的遭遇。王唯真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杯水,抓起桌上的电话找到政工组的苏群,请他给河南分社的刘建生打电话,王唯真说:第一,陈健同志到总社来反映分社运动情况合理合法;第二,她是普通记者,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对象;第三,她来北京的往返路费回去要给她报销;第四,分社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强制她劳动,她回去后应正常参加文化大革命。他还告诉苏群:“或是给招待所打个招呼,或是给她写个便条,她现在急需住下休息……”王唯真打电话时没有分一二三四,是我写时分开的,但上边的意思都说到了,大都是原话。
我回到分社,上述意见都落实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获得人身自由,这件事轰动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所属单位的所在区。分社周围的新闻、出版、电台、文艺、社科院等单位,有我好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原先的处境一样,被认为是“漏网”右派,当我的这些朋友还没有“解放”而知道我“凯旋”归来时,暗中串连、奔走相告,王唯真的大名也不胫而走。
最高兴的是我的孩子们,之前他们在院子里,碰见大人、孩子不敢抬头。妈妈没有出入大门的自由,奶奶被赶走,没有人给他们做饭。当时,即便大部分供应杂粮,每家每月二斤猪肉、半斤油,妈妈能去市场买回调理出“可口”的饭菜,按时让他们吃饱。他们小小的年纪说不出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高兴,但能意识到妈妈是这个家的灵魂。
“灵魂”自由了,真好!那怕是一点点人身自由,当时也感觉是一步登天。
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周原五十年代就被反右的大棒当头一击,几乎把我们一家击碎。幸运的是我们虽屡遭小人陷害,也屡有贵人相助,才得以生存下来,王唯真是其中之一。文革八年,河南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轮流坐庄,我们的处境时好时坏,当周原为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要被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书记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当年,穆青命周原向河南省委汇报豫东之行、主要汇报焦裕禄的事迹和宣读他写的通讯初稿时,听汇报的就是纪登奎。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吗!”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穆青被解放时倒也说了一句实话:“没想到焦裕禄解放了我。”

周原陈健夫妇(右一、二)和王唯真陈萍参加新华社离休干部活动在圆明园留影。
虽然,我和周原与王唯真友谊的建立,是文革中的这次解救,但由于我们在河南,他在北京,后来我们一家调到北京,又由于住处相距很远,来往交谈并不多,但这些阻隔,并没有妨碍我们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一位可交心、交底的老同志。
王唯真的思想理念,文化素养、视野和胸怀,使他不像一些人复杂得难以沟通。相反,他更简单透明。新华社的两位老前辈彭迪、庄重,对他有入木三分的评价,前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单纯。”后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厚道。”王唯真受父母的影响,也许还包括遗传基因,他除却上述的优点外,还具有非常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些综合素质,把他和一些干部区别开来,也被某些领导所不欣赏。前边说过,王唯真的艰苦朴素,不是来自老传统,而是来自他的信仰和做人的良知。陈萍告诉我,王唯真除响应国家号召把存款捐给灾区难民之外,还随时随地对难侨或他们的子女,给予经济上、物质上的救助。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为老干部创造了一个闪亮的词儿叫“两头真”,已被广泛认同和运用。说的是有些老干部,起初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参加了共产党,经过漫长的崎岖的人生坎坷,到老来又回到起点重新追求民主、自由。这样的老干部故然可尊可敬,但毕竟是少数。我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王唯真是否“两头真”,但他的“一头真”也真得令人肃然起敬。可怕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两头假”的干部,终其一生,为了追求个人的权势和名位,都戴着假面具,或者如川剧中的“变脸”,让人看不清真面目。这种人,不露声色地滑过道道阻险难关,却能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甚至堪称“楷模”。
王唯真弥留时,我去医院看他,选了几支白色的百合,外用淡紫色纱纸托裹着。陈萍捧过花束转向王唯真,他凝神望着,两眼清亮有神,脸上放出奇异的光彩。我被感动了,对病床前的男孩说:“你外公年轻时可是一表人才!”陈萍接着说:“他现在也是一表人才啊。”王唯真留给他的亲人们和友人的,是一个美丽的形象。
节选自文章《 父与子——深切悼念王唯真同志 》
作者简介:新华社资深记者,1928年2月出生在安徽宿县,1949年调任 新华社记者直至离休。采写过大量新闻通讯,并在全国多家大型文艺刊物、 《人民日报》等副刊、《炎黄春秋》、《随笔》等杂志,发表过报告文学、散文 、回忆录等;有些通讯、散文、人物专访分别被中学课本、人民大学新闻系选为辅导教材。她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有的已被香港出版的文集收入。
来源:2007年《炎黄春秋》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