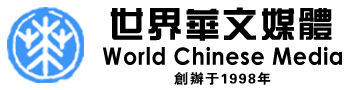记美洲华人文艺刊物《红杉林》
《红杉林》从2006春天诞生,到2008年春季号,一共出版了八期。主编吕红问我是否有兴趣就《红杉林》创刊以来的散文和诗歌写一篇评论,我没有仔细权衡,就答应下来了。及至着手去干这件事,才发现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干的事。散文是一个极为宽泛的分类,状物写景、感触心得、人物特写、游记日记等等都可以统摄为散文,要一一去品味,说出点子丑寅卯,就有了些千头万绪的感觉。至于诗歌,虽然就其排列形式而言,容易区分一些,但其内容却是飘忽得不容易琢磨的。正像艾略特说过的那样,诗难理解,因为诗人写诗时不得不省略很多逻辑步骤。所以,要品诗,还要说出究竟;要一一读了,且有所领会,却也不是手到擒来的。然而既已答应下来,就覆水难收,只有勉力去做了。
在《红杉林》上刊载的散文中,写文人的占了好大篇幅。从创刊号上北岛的《帕拉与聂鲁达-智利散记之一》和苏炜的《千岁之约》以及阙维杭的《永远的惠特曼》开始,到后来李硕儒的《繁华未尽已凋零》和王学信的《阿成印象》等都可以归为这类范畴。
北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以诗歌名满天下的,他诗歌中的很多句子至今还为人们所铭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类句子就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名句一样,为人们评说人物时所津津乐道。诗人可以把句子锤炼成诗句,也可以闲散地把句子连缀成美文。在他的笔下,聂鲁达变得生动了,仿佛就在他的黑岛复活过来,面对大海吟诵,向我们展现他富有魅力的革命斗志和浪漫情怀。北岛的笔触时而指向历史深处,时而回到现实;时而描述生活,时而谈论文章,却不露声色,不着痕迹,显示了他高超的文字素养和玄妙的脉理思路。
阙维杭笔下的惠特曼也有革命性的一面,从诗句到内容,惠特曼都是一个蓬勃的革命者。我在准备高考的那段日子里,曾经在很多个午睡前的几分钟里,读过《草叶集》,惠特曼那些长而流畅的诗句,铺陈得如海上汹涌而来的波涛,读起来让人荡气回肠。好多年过去了,他的诗句如今记不住一句,但当初读他的诗的感觉却还崭新如故。惠特曼虽然是个故知,却从来没有对他的诗歌有过理性层次的认识。现在,读了阙维杭的文章,对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他的诗风以及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才第一次有了一点了解。
阿成是中国文人都知晓的一个文人,他当初的三王系列让他名声鹊起。阿成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他的语言很有争议,有人说他的语言是挤出来的,读起来疙瘩。也有人说他的语言有着拙朴之美。这正好说明,他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阿成到美国都超过二十年了,听说他在美国活得不容易,好长一段时间就以车为家,曾经搬过不计其数的家。王学信以老同学老兵团战士的身份,把一个内向沉稳、学识渊博的阿成介绍给了我们。通过《阿成印象》,我们知道,阿成好像是偶然成为一个文学大家的,在朋友的聚会中,他从容地聊起了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的生活,绘声绘色地谈起了那里一个一个有趣的人物。听众被感染了,于是鼓励他把这些人物写出来,这就有了三王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写出来了之后,阿成的朋友们看了,就悄悄地替他投稿了,这样,作家阿成就塑造出来了。阿成的作家之路看起来不在设计之中,不是主观意愿,但是,又有着某种必然性。他的家庭,他从小浸淫其中的书香环境,以及他的博览群书,使得他的作品不过是厚积薄发的产物而已。
《繁华未尽已凋零》告诉的是一个凄凉的故事。同样经历了体力劳动的洗礼,同样到了美利坚,还曾经在文坛意气风发,先做中文副刊主编,后来开办公司,在经商之路上正阔步前进的时候,刘维群却突然撒手西归。在李硕儒的笔下,刘维群是个古道热肠的湖南汉子,一个热忱的文人,有着超凡脱俗的文学理想。灾难降临到刘维群的头上,是人世间一件很残酷的事,让同样从事中文写作的我们,不禁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在异国,要从事中文写作或编辑出版,本来就像苦行僧一样清苦,如果只是清苦而已,却有一份平实、欢乐和健康,那也是很不错的一种境界。不幸的是,像刘维群这样好的文人,却会遭受如此落难,读完这篇,由不得不扼腕叹息。
所以,人即使不是太得意,也要像李白说的那样“须尽欢”。《千岁之约》渲染烘托的正是这样一种文人作乐的场面。在诗人北岛家暖融融红彤彤的壁炉前,一群文人歌而蹈之,唱着故国悠远豪迈的民歌,甚至裹着羊毛肚毛巾摇头晃脑,即使没有亲历现场,也不能不被感染。苏炜的文笔欢快而恣肆,这篇文人的聚会散文读得人全身发热,血也有些沸腾了。
苏炜的另外一篇散文《金陵访琴》也染着他一贯的欢快气息,但却透露出儒雅和书卷气。中国传统文人对于琴有着一种近乎图腾的崇敬。所以,他在文章的标题里对琴用了“访”这个尊敬的字眼,俨然把琴拟人化为一个可尊敬的对象,可谓用心良苦。这篇散文篇幅较长,却不嫌罗嗦,谈起琴来,引经据典,表现出作者对琴史、琴理的了然于心。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作者在琴师郭平家里听琴得琴那段。郭平在琴房里,为他演奏了千古传颂的《流水》。一曲听罢,作者“一时百感会心。我只是沉默着,不说话,好像特意为琴音留一个回旋的空间,心神还羁留在那萦绕不去的流水之中。”听琴的美好感受还没有化去,另一个幸福又接踵而来。琴师要赠给他一床琴,而且任他选。苏炜选中了“霜钟”。他抱着琴,“像是抱着一个初生的婴儿,一身的细润娇嫩,左右上下端详个不够,一时竟有些不敢置信的真是个‘一琴在手,蓬荜生辉’!我乐呵呵、傻呵呵地抱着琴,抚着琴,在屋里兜着圈子,一时真觉得眼前的空间豁亮了,高旷了,落霞变成调色盘,小小雅室,一下子烟霞滚滚,变成万松之壑、万川之流了。”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苏炜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我不能不为他高兴!
既然扯到了艺术,那就姑且顺着这条思路去读吕红的《森林中的白马》。
吕红谈东山魁夷的画,由头是一个青年画家当初赠给作者的一幅临摹画。临摹的当然是东山魁夷。那个青年画家为了一个久远的梦,远行。临别前,就把这幅画作为一个告别赠送。画中,茂密的森林是远景,近境是平静如镜的湖面,一匹白马在湖和林之间徘徊,像是在思考,像是在酝酿某个新的目的地。照作者的理解,这幅画表现的就是梦,关乎人生,关乎自然。吕红从这幅画谈起,却不以这幅画为终结。她在北京逛书店时,看到了东山魁夷的画册,爱不释手,就毅然买下。所以,在这篇文字里,其笔触所至,东山魁夷的风格就被丝丝入扣地揭示出来。
《森林中的白马》对画面有着富有层次的感悟,让读者欣赏着画家的绘画风格,也欣赏着作家的散文风格。吕红的小说中,常常有大段的散文化铺陈。这篇散文中自谓为“你”,却也特别,读着就有了些小说的意味。吕红在创作的时候,原来是在小说和散文这两种体裁间自由跳跃的。
前面那些写人物的散文着墨在文人上,而且其中许多文人都是闻达之人。依娃、蓓蓓和余雪却把目光放在了自己普通的亲人身上。依娃的《妹子》通过妹妹跟自己不同的人生境遇,发清b了人的命运的偶然性,或者说发现了环境对人制约的必然性。当初,只是因为省一张嘴,作者跟妹妹由城里亲戚家选择收养,自己成了幸运者。由此,就进了城,最后还出了国。而妹妹却成了一个农妇。她们之间以后的不同不是因了自己的造化,而是因了城乡间的巨大壁垒。在她的《万里归来祭父魂》中,她以深情的笔触向我们介绍了她质朴的父亲,一个黄土高原的老农,一个未老先衰的一家之主。依娃成了城里人,却对生她养她的父亲,对曾经一同成长的妹妹充满了爱和尊敬,这种情怀实在可敬可佩。她的文笔真诚细腻,真情真爱都从心间流淌出来,灌注于文字之间。读了不能不怦然心动。
蓓蓓的散文中,飘着浓烈的贵州乡土气息,读来格外别致和亲切。《对一个无声世界的怀念》的字句和情绪就像贵阳市郊花溪的水,清丽可人,潺潺不息。她对一些概念、场景和意象的描述,充沛而丰厚。比如,关于上班,在每一个人那里是表现得截然不一的。苹果是她家的大堆积,但在那个出门的日子里,那个苹果又是如此稀缺金贵。她的很多描述生动新奇得让人拍案叫绝。比如:“他常常出去钓鱼,从早钓到晚,把太阳和月亮统统钓落,可他从来没有钓到过鱼。”又比如:“电话拨通了。婷的语调很是热情。一点也不像我的记忆里那个墙一样足以堵死去路的影子。”还比如:“她独白式的语言,把一条噩耗压得平平展展,服服帖帖的,就像她没有一丝纹路,青春洋溢的脸。”贵州虽然穷,但那里陡险的山清亮的水就像艺术的养分,滋养了好多不凡的艺术家。歌唱、绘画以及写作这些领域里,常有不俗的人从贵州走来。
被人称为湾区余秋雨的朱琦果然名不虚传,他写的《问(牡丹亭),情为何物》旁征博引,把《牡丹亭》问世的前前后后、汤显祖的初衷和后人对《牡丹亭》的痴迷娓娓道来,让人大长见识。朱琦在此文中还花了大量文字来说明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却也有着人性的暗潮汹涌,并试图用当时都市经济的繁荣来说明这种人欲跟灭人欲理论的不对称。且不论他是否揭示了这种不对称的历史成因,单就这种不对称而言,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个时期还是中国历史上性文化发达的一个时期,比如《素娥篇》就是那个时候问世的,如果一定要去追究其中原因,经济发达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上层建筑的松散直接给予了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明末,朝纲已经败坏,所以统治者也顾不得来控制人民的精神创造了。这种情形跟宋朝的相仿。宋朝统治者昏聩软弱,反倒提供了一个理论蜂起、学派林立的兴盛局面。
东方人家庭中的长辈跟下辈的关系多有壁垒森严。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早就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固着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庭里。正因为如此,余雪的《女儿》把一个母亲跟女儿之间亲切平等的关系,通过一个一个场景表现出来,读来让人感佩。
辛哥的《家居黄页》不管是「空城计」也好,是《不得不说谎》还是《人生次序》也罢,宣示的是另外一种滋味。散文家刘荒田在他的《旧赋》中,以沉郁辛酸的笔调回溯文人在异乡执着于故国文字的艰难,用中文写文章,出版中文刊物报纸,竟然有了唐吉科德一样的悲壮和荒诞。在《填空式书写:新历除夕》中,他则以细密的笔法把除夕那天的所见所闻都一一记载下来,很多场景,我们都熟视无睹的,在他的笔下,却有了另外一番意义和出人意料的新奇。仿佛观测同一个物事,我们看到的只是两维,他却揭示了三维。
亢霓的《山幽月明时》把山中一个美仑美奂的中秋夜形之于笔端。在日益都市化的今天,回到山野,原来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文中的晓北从海外回到故国,却又不留在繁华的都市,而像古时的高人,息影山林,独得清幽。让人不由生出许多羡慕。
喻丽清是我喜欢的一个散文大家。很早以前读过她一篇小文,虽然篇幅不大,却跌宕起伏,发人深省,让人耳目一新。后来每逢她的文字,总要流连一番。她在《红杉林》上发表的《都是雷暴惹的祸》却一反以往风格,以平铺直叙的手法把旅途中的不顺告诉给读者。
秦婕的《感动与困惑》读了之后,让人跟着作者一道深思。一些貌似平白成为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另外的背景下,有了从另外一个全新角度诠释的可能性。
此外,《红杉林》上发表的诗歌于数量上讲,不是太多;从形式上论,像是点缀。但是,这些诗歌中,很多是值得品味再三的。
在《红杉林》上,我首先读到的诗歌是郑愁予的《水巷》和《归航曲》。他的名字可以咀嚼,他的诗句更让人不得不一再地读下去,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美妙。“四周的青山太高了,显得晴空/如一描蓝的窗àà/我们常常拉上云的窗帷/那是阴了,而且飘着雨的流苏”就这几句,我读啊读,读得意犹未尽。后来一个金色午后,我在电话里对着一个朋友朗诵了这几句,也把对方感动了,于是就在网上寻了更多的郑诗来读,一样喜欢。郑愁予的诗就像撩拨人的小曲,节奏徐缓,一唱三叹,读着读着,人就进入了一种迷醉的诗意状态。
老诗人写的爱情诗也许是他年轻时候写的,但知道他如今已经90高寿,看着照片上的他如苍劲的青松,心里的感动竟然无以复加。纪弦的《你的名字》读起来,由弱渐强,由低渐高。虽然在诗中用到了十二个轻字来呼唤“你的名字“,情绪却像风帆一样被诗中旋律的长风鼓满,充沛得在低音区强劲地激荡。“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日每夜 / 写你的名字/画你的名字/而梦见的是你发光的名字”。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如此着魔般在乎和想念,也许会让凡夫俗子们嘲笑,但这种痴情才真是超凡脱俗的人间至情。
才读了张错的《山居》的前两句,我就被他的那种恬淡的家常气息所感染。“默默淘米煮饭/再把卷心菜一刀切了”。句子平实如直白一般,却也生动,把山居的平静日子烘托而出。“清晨推窗,/有雪,佳。/去夕,暮色强掩夕阳,/无妨”这两句把山居中人的随意心情表达得贴切而生动。
施雨是写小说的,但却是从写诗歌起家。以前,没有好好读过她的诗歌。因为写这篇文字,才读了《红杉林》上登载的几首。一读,却不由一震。她在诗中把比附手法用得娴熟自如。比如:“夏日的葡萄,卷曲着所有的新意/黑白相间的琴键,是阴晴不定的季节。”在她的诗中,强烈的对比随处可见,使得她要表达的情绪更具感染力。比如“每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总是小心收紧自己/让教堂的尖顶去支撑天空/我只要一间亮着灯光的小屋。”这一句也很精彩:“擦肩而过/笔是笔 墨是墨/白纸上不会留下风雨阴晴。”
四季原来是有性别的,两男两女。春天是浪漫的女孩子,夏天是爽健的男孩子,秋天是优雅的夫人,冬天是威厉的将军。这不是我的发现,是曾铭在《四季的肖像》中的宣示。诗不仅要有形式的美,而且要能传达某种内容某种旨趣。曾铭的诗除了形式上的工整,还不拘于形式,赋予某种意象以多重的意义。《我的月亮》分为九阙对月亮作了九个描述,却能做到不重复不累赘,委实不易。
读王性初的《寒窗》,八十年代读朦胧诗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的诗充满了意象,意象之间好像都独立,并没有递进的关系。这首诗是诗人赴美十周年写的,显然是对十年异乡生涯的一个总结或者感叹,但诗句间并没有直露地表达什么,一切情绪都通过隐讳的诗句来宣示。“将熟悉抵押给日后的陌生”仿佛是指抛弃了自己熟悉的文化习俗环境,到了全新的美利坚。但这也只是读者的意会而已。诗的末尾一句“扯下窗帘又是一个世纪的睡意”传达出几分潇洒和通达。
非马是诗歌王国里的一棵常青树,创作生涯漫长而硕果累累,如今,他已经著有诗集十四种。非马的诗少有低吟浅唱,更多的是某种深沉的思考。他的很多诗句就像古希腊哲人的沉吟。在《芝加哥之冬》中,他以室内电视上的春天景像跟室外的冰雪压弯的老树作对比,读来不免震撼。同样是说杨翁之间的婚恋,非马却以他的思辨写出了《82-28》这样的小诗,把近代数学和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巧妙地应用在诗中,值得玩味。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诗是最精致的,一字一句都有讲究,字斟句酌在作诗的时候才真正达到了极致。受过严格数学训练的小平写着自由的诗篇,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数学思维要严谨,诗歌情怀要飞扬,数学和诗歌这两者之间看起来是如此水火不容。形式严谨的格律诗本来对数学还有的某种包容,在新诗这里却似乎丧失殆尽。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对立其实是不能抹去深层结构的共通的。语义哲学家早就认为不同语言之间在深层结构是一脉相通的。数学语言和诗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概莫能外。小平对诗句的营造和对营造出来的诗句增减的坚守,跟她的数学背景大有关联。
《我的河》跟《在此相遇》写的是某种微妙的倾诉,字句之间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某种情愫,让人可以琢磨,却又不得要领。小平的诗风含蓄隐讳高远,大量应用隐喻,以飘渺的手法轻歌曼舞。破译小平的诗句是件愉快的的事,之所以愉快,是因为那是一个再创造。她怎么样想的,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她给予了读者想象的暗示和空间。在《我的河》中,“写诗的女人/一旦/爱上了自己的爱/千年的蛊惑/便肆意穿梭夜色”这几句说了爱这个原因,却道出了蛊惑肆意穿梭夜色这个结果。读起来有些费解,再一细想,才似乎明白了诗人要说的是,爱让人辗转而不得眠。用一种对立的手法来表达,也是小平酷爱的,比如:“虚幻得如此真实/那么就相约吧/约好了在寂寞里散步/在蓝色的第五季/站成窗口彼此凝望的旅人”。虚幻跟真实是对立的,但却也相通,在某个论域里,虚幻就是真实。那么第五季呢?季节只有四季,第五季显然是一种虚无。在这样的季节里相望,就成了一种梦境。这样的梦境不再有任何维度的羁绊,以精神的形式长存。
《红杉林》上的其它散文和诗歌鉴于篇幅,无法一一提及,读的时候却是感喟不已的。
在海外出版中文杂志,是一个壮举。《红杉林》这个壮举已经持续了两年余,因为了主编副主编及其他编务人员的辛苦,因为各界的慷慨相助,多少名篇佳作才以黑字白纸的形式优雅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读着《红杉林》,心里就不由祈祷,但愿她走得更远!

(2008年0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