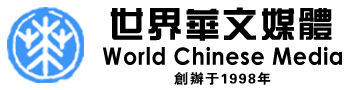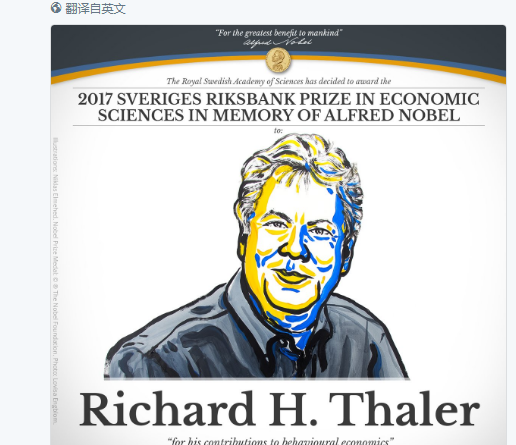泰勒获诺奖,经济两导向
泰勒获诺奖,经济两导向
——“民本位经济学”新时代为“仨自组织人”鸣锣开道
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9日11:45,2017年诺贝奖经济学奖正式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因对违反或背离“理性人假设”的人类经济行为(系统性偏离理性行为的“行为”)研究的贡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一经济学颁奖,具有经济学的导向意义。这个导向意义至少在两点上是明确的:一是标志着经济学将开创“民本位”的新时代,一是泰勒发现的“有限理性与禀赋效应”(基于系统性偏离理性人假设),为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将“仨自组织人”作为理论起点,提供了从理论和经验论据上的支持。
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
按照我在《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一书中对经济学的理解,尽管认知方法和参与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也应当像物理学那样,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而非划分为“井水不患河水”似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需要处理宏观与微观的问题,而宏观与微观并不能代替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分工。
那么,如行为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显然都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
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当初将伦理学嫁接到经济学并应用到国民经济行为研究中一样,1978年诺奖得主西蒙(Herbert A.Simon)、2002年诺奖得主史密斯(Vernon Lomax Smith)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及其合作伙伴特沃斯基(Daniel Kahneman)、2013年诺奖得主席勒(RobertJ.Shiller)等不满足“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都将心理学嫁接到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之中,直接诉诸大众投资者“非理性”参与金融博弈。今年的经济学诺奖得主理查德•泰勒在行为经济学上的贡献,也是将心理学嫁接到经济学研究中,应用于消费者行为和政府政策之外的,对民众更为具体而重要的金融投资理财决策,如资产价值如何评估才合理,群体性心理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效应,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应该怎么平衡等等。
正如财经评论员杨国英接受凤凰网财经采访时所挑明的:“理查德•泰勒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市场大众投资者的决策参考,只要你用心咀嚼、潜心思考,绝对会有一字千金的收获。”比如,理查德•泰勒根据投资者对过去输者组合过分悲观,对过去的赢者组合过分乐观,导致股价偏离其基本价值,待一段时间之后市场自动修正,前期的输者将赢得正的超额收益,前期赢者的超额收益则为负现象,提出“输者赢者效应”,作为博弈股票收益的新方法,即采用“反转策略”,买进过去3至5年内输者组合,卖出赢者组合,这一策略可以使投资者在未来3至5年内获得超额收益。
如果说,可以把分别对于小皮特首相、罗斯福总统、里根总统的政策实践都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亚当•斯密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芝加哥学派和弗里得曼经济学,称之为“官本位”的经济学旧时代的话,那么,自2012年罗斯(Alvin E. Roth)和沙普利(Lloyd Stowell Shapley),2013年金・法马(Jinfama)、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席勒(Robert J. Shiller),至2017年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再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妨看作是经济学的“民本位”新时代的开始。
这里请允许我稍稍偏离本文主题,引述一下2009年8月3日我在“《第二次革命——里根经济学》再版研讨会上的发言”《回归完整的亚当•斯密主义》中的一段话:
[从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这就是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新古典综合派,到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经济学中的大家,往往都不只是单纯具有经济学的素养,或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大凡在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领域卓有建树者,都具有哲学、伦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否则,一个国家或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就只有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作钟摆式选择,经济学家只需根据政府实施什么样的政策而专注于技术层面的完善,或者为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作注释。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及其宏观经济学的丧钟就已经敲响!]
我当时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将让位于“社会学”的更加深入广延的展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学必将从“政府本位”“官本位”转向“社会本位”“民本位”。
显然,民本位的经济学新时代,不只是需要“民本位的应用经济学”,而且目前仅限于其他学科的嫁接应用范畴,更需要“民本位的理论经济学”,或者说,由于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主权国家世界秩序下的各国经济,基本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二元对立世纪钟摆”困境而难以自拔,亟需更具综合性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问世。政府与社会、官家与民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经济学家们的无私帮助。
因此,这是一种综合并“超越了官本位与民本位”的理论经济学。在我看来,就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研究的共生经济学理论体系”(2010)。
仨自组织人与共生权范式
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而问题在于脱离生活常態的生产与超限资本增值,已然超越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改变何以可能?这就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
当我提出:“社会学将取代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命题,并发问:“共生论”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时,就注定了“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一词在其概念构词中,已经是“社会论”或“社会科学”(漆琪生)的,也是“经世济民学”(陈岱孙)的,而且既是具有哲学意味,又能具体化为政策制度和大众实践。所以,《共生经济学•绪论》的标题是《作为社会哲学的“当代经济学”刍议》。
因此,只是考察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及相应的“五次分配”2方式,即运行的制度禀赋基础,远不足以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真实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禀赋诉求的同时性问题——亦即卡尼曼、特沃斯基和泰勒等人发现的真实的人对于理性人的“系统性偏离”现象。
特别是经济运行中涉及到与“制度-文化-人性”直接关联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关系的实时处理时,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单纯经济学思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扩大到存在各种“偏好”的社会生活万象,不仅像鼻祖亚当•斯密当初借用伦理学建构经济学;像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借用社会学完成基于“(劳资)阶级人假设”的经济学;像科斯(Ronald H. Coase)借用法学提出基于“产权清晰-零交易成本假设”的经济学;像西蒙、史密斯、卡尼曼、沃斯基和泰勒借用心理学弥补经济学的不足;像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借用文化人类学重构伙伴经济学,或者将有人继续这些思路接着借用政治学、理论物理学、生態学的方法拓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而且,在我看来,更要上升到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和“追寻可能的世界”的哲学上,加以全面观照,才能找到合适的经济学方法。
由此可知,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嫁接或应用,是亚当•斯密创立经济学之初及此后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常態,而如果人类在哲学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却可能引发经济学革命。
共生哲学认为,每个人生而具有认知和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自组织灵动力,同时又处于你、我、他(她、它、祂)动態平衡的关系过程之中。而且,凡是身心灵健康完整的人,都生而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三大诉求的均衡禀赋,都有在单位时间内追求成本最低而尊严感最强、幸福度最高的臻美禀赋。
共生经济学作为理论起点的“仨自组织人”,正是共生哲学的自然理论延伸。这里,我将北方话中的“仨”上升为哲学、经济概念1。仨自组织人中的“仨”,指政治、经济、文化三种诉求的同时性,也指你、我、他(她、它、祂)关系过程;仨自组织人中“自”,指自组织灵动力。
借用“天赋人权”的表达,世间万物都有天赋生命自组织灵动力的共生之权。共生之权,是将包括每种生灵(包括野生动植物)、每个人、每种共同体,都有免于遭受严重的贫穷、饥饿,因而富有尊严获得幸福的权利涵盖其中。共生智慧,不舍弃任何人。所以,我们将基于宪政制序“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Symbiorights)。
共生权,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钱宏2010)建构的共生经济学2基础概念之一。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
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范式,是对“共产”“大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官粹(本位)”与“民粹(本位)”这种两极对立思维的选择性“政治正确”的超越与融合,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特权(权力资本)的纠结。
这样,共生权范式,就成为人民、国民、公民、社会,保留对强势产权者进行革命“底线权”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 何兆武、习近平,2012)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状况,进行实时揭露曝光,实施有序改革、改良、改变,使之实时恢复live and let live活力,实现同处蓝天下的人民win-win-win的正常状况的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美国电影《哈里之战》,还是2014年5月内华达居民武装对抗“强拆”上演的现实版“哈里之战”,都是对“共生权”底线思维的鲜活图解!
共生权,也是综合中国群经之首《易经》“生生之德,进退之道,损益之法”和古希腊文艺复兴“自由理性与爱的践约”智慧,强调强者(官)自律、弱者(民)自励,官知“道之进退”,民谙“生之厚德”,“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知进退”是一种由共生智慧派生的善恶观,就是如弘一法师所说的“势可为恶而不为即是善,力可行善而不行即是恶”,加上两条,一是“结党营私而不营即是公,立党为公而不为即是私”,一是“法许可作而不作即非善政,法禁止作而狂作即非良治”。
共生权定位下的依法治国,就是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边界,因此,需要以宪法及宪法法院为法理实践基础,确立解套“中国模式萧何定律”的三大法典:第一,是规范公仆、管家行为的《官法典》,废除《八二宪法》第9、10、15条,以《反操(控)纵法》、《行政许可法》为基础;第二,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以《八二宪法》第2、33、35、41条为前提条件,并新制订《国民事权法》为基础;第三,惩治官、民越位、越界行为的《刑法典》,以《刑事诉讼法》,并新制订《赎买特赦法》为基础。
共生经济学及其现实应用
我所谓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起因,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前“两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先生与我讨论“生態文明”和“生態经济”价值参量,应当与“工商文明”和“工商经济”形態有所不同的通讯中,提出来的概念。
当我2010年6月8日在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接受特聘研究员3,第一次讲述把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注入经济学基础理论时,因2009年3月应杨鲁军邀请为他的《里根经济学》再版作序,受Reaganomics先例的启发,我就想为这个新兴的共生经济学造一个英文单词。Sym-bio-nomics这个词,也是由“共生论”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和经济学economics组合而来。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词头“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已经有“社会”(society)的意味;二是中间的“bio”,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三是后缀“nomics”,意为“经济学”(economics),和合而成英文Symbionomics,来对译中文共生经济学。
从共生哲学上看,解套“中国模式萧何定律”的三大法典,属于恊同学的平衡制衡均衡机制,而共生经济学的现实应用,则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动力学托底机制。
共生经济学,具备这样三大特征:
A,将理性经济人的“投资-消费-进出口”,转换为以仨自组织人的“生产-交换-生活”为理论出发点;
B,将“产業”转换为“生態”即全生態经济学版图,顺势将“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二元对立形態,扩展为“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
C,将资本增值/减值的GDP价值参量,转换为资源能效/能耗的GDE价值参量。
所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要求以“估自组织人”为理论基点,以“共生权”为法权基础,以开源社区、“共生链”(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经济”维度,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
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以欧洲为标志;
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成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4。
关于共生经济学,先说这么多,有兴趣了解共生思维和共生价值观的朋友可以加我们全球共生研究院的公众号IGS1218与上海三联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共生经济学》。
生態文明如何做到位?
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特别是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写到这里,我得先说说俄罗斯。我知道,世界上特别是中国,有许多人不看好俄罗斯。这里不妨说说我的感受。我曾有幸于2001年和2009年两度应邀赴俄考察,得到的总体印象为:俄罗斯是一个超稳定的国度。有着强大的国防力量及其军工企业的俄罗斯,短缺的不过是轻工电子产品和奢侈品,以及跨国金融资本服务。但这又涉及到现代、后现代的必要性,或现代化的度的问题6。
我看到的是:在俄罗斯国民高雅文化追求的底部,是城乡居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片大小不等的土地、一幢“别墅”(当然没有中国富豪们宽绰,有的还只是一个像美国西部居民那样的小木屋)和一辆拉达车,特别是,在面包、牛奶和皮货等生活必须品充分自给的条件下,他们还有充分而富有情致的天王老子都管不着的与GDP增长率没有关系的有序的社区(乡村)生活——可望自觉实行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以“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超越世界经济体系“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二元对立的世纪性钟摆状况。
如果把遍布俄罗斯的“社区(乡村)生活”作为一面镜子,正好照出美国(城市空心化)和中国(乡村生活败落)的大问题!
当然,近年来中美两国民间,都有些超越“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自发组织行为的迹象,这就是美国的“新经济运动”和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而且,美国的“新经济运动”和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参与者们还有一个共识,即:生態文明意识!
众所周知,中国是最早把“生態文明建设”写进执政党战略的国度(2007)。而且,2008年底国务还批准在中国江西设立了一个“鄱阳湖生態经济实验区”,只是作为一个国家战略,至今未能真正运行起来。这是因为人们对“生態文明”的概念,特别生態文明的哲学支撑、经济学价值参量,尚不十分了然,以及思维路径依赖与既得利益羁绊所致。
许多人士,至今没有跳出“园区经济模式”的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比如最近有篇给“雄安新区”发展支招的文章叫《传统园区模式已死,“产业引领+基金操盘”时代到来!》,是人民日报记者对上海张江高科总经理葛培健先生的一篇采访。
采访者和受访者,确实看到了:“传统园区模式,往往是以土地财政、房地产驱动和土地资源买卖为基本框架,不可否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过贡献,但弊端和后遗症同样明显。在新常态下,如果继续这种模式,无异于竭泽而渔,饮鸩止渴。”这是因为土地财政的本质是“土地空转”“发展”融资,而“资”的本质永远是“债”,“欠债还钱”是天理,若债台高筑,就会导致“破产”,但“破产”对国家是不可承受之重。可是,即使“雄安新区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信号,那就是传统园区模式即将走向终结”,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以税收财政、产业创新引领和创新资源流动为基本框架的新型园区模式”吗?
税收财政、资源流动、“产业引领+基金操盘”,能救活已死的中国特色园区经济模式吗?中国搞了近四十年的大大小小各种园区模式,既然已经死了,即使给这些个园区经济插入吊命的“气食管”,能够达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目的吗?我只想说,只要着力点不放在“上层建筑规模与结构超越经济基础负荷与阈值”这一根本性现实矛盾上,无论是所谓西方式金融工具,还是中国式政策谋略,比如争执从“土地财政”转到“税收财政”,以及是“直接税”好,还是“间接税”好;是提高“税率”好,还是扩大“税基”好(Laffer Curve);是“规范产业政策”好,还是“城乡的统筹规划”好,诸如此类的讨论,也许都尚可延缓“破产”,但都终将无解!
以“土地财政”为标志的政府推动的园区经济模式,走过近四十个年头(即使从浦东新区算起也二十五年了),到如今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死结,转不动了,不灵了,不如顺势让它“安息转化”!
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观之,“安息转化”的解套办法也许相对简单,比如把葛培健总经理的公式变换一下内容,即与“官本位”的财政经济思维和价值取向脱钩,将“产业引领+基金操盘”转换为“基金操盘+生態引领”方式7,实施“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战略转型。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千年大计”承接北京“非首都双创”功能的雄安新区,完全可以成为这一新经济形態的实践表率——亦即“生態统领,共生为魂”,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表率!
最近,中国江西再次传来一个好消息——国务院决定在江西直接设立“生態文明实验区”的决定。这事与我有一些内在联系,我衷心希望主事者能克服过去的认知局限和参与障碍。
我相信,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成长的格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全面展开之日,就是中国执政党率先全球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设”成为人类全新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之时。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从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向生態文明先发国度的华丽转型!
盘点近十一年来的经济学诺奖
最后,我们看看近十一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都颁给了谁?
2006年,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因其“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埃德蒙•费尔普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指出通货膨胀不仅和失业率有关,也跟企业及雇员对价格的预期有关,并将基于理性预期的经济学分析引入到就业决定理论与“工资-价格动态均衡”,并提出经济增长的“资本累积黄金定律”等。2014年5月,我有幸与埃德蒙•费尔普斯在上海交通大学相遇,并讨论增长的极限问题,事后作《从“增长黄金率”到“健康黄金率”刍议——共生经济学VS诺贝尔奖得主费尔普斯》(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4年第21期)。
2007年,美国经济学家赫维奇(Leonid Hurwicz)、马斯金(Eric Maskin)和迈尔森(Roger B. Myerson)。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 “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
200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克鲁格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他的新理论能够帮助解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驱动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分析可用于解释大多数社会组织形式。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揭示了使用者组织是如何有效管理公共资源的。威廉森的研究则发展了有关公司作为一些架构安排解决利益冲突的理论。
2010年,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Peter A.Diamond)、莫滕森(Dale T.Mortensen),以及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皮萨里季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分享这一奖项。这三名经济学家凭借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理论的进一步分析,摘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三人的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包括“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三人建立的经济模型还有助于人们理解“规章制度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
201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以及纽约大学萨金特 (Thomas J.Sargent)。西姆斯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对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和应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面。他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作用,反映出对宏观政策效果的关注。而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研究领域均有建树。
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思( Alvin E.Roth)与沙普利( Lloyd S.Shapley),以表彰他们在“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的贡献。沙普利采用了所谓的合作博弈理论并比较了不同的匹配方法。其研究重点是如何使双方不愿打破当前的匹配状态,以保持匹配的稳定性。罗思的贡献在于,他发现沙普利的理论能够阐明一些重要市场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通过一系列研究,他发现“稳定”是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功的关键因素。
2013年,美国经济学家金・法马(Jin fama)、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席勒(Robert J. Shiller),他们因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取得显著成就而获此殊荣。评选委员会指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人们目前对资产价格理解的基础,资产价格一方面依赖波动风险和风险态度,另一方面也与非理性行为偏差和市场摩擦相关。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他被誉为当代“天才经济学家”,累计发表过300多篇论文和11本专著。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监管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并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
2015年,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知名微观经济学家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以此来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更加有效地制定反贫困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哈佛大学的哈特(Oliver har)、麻省理工学院的霍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获奖理由是他们对契约理论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与制度,以及契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十分具有价值。
2017年诺贝奖经济学奖正式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因对对违反或背离“理性人假设”的人类经济行为研究的贡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后,当我们回顾诺奖得主,结合当代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境时,我再次想起,当年,作为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先生,是注意到了人除了专注专业化提高技能的“理性人”一面外,还有关心公平、正义的道德情操的一面,所以,告诫世人和小皮特首相的话:国家的财富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小皮特就是那位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比喻,来说明平民的基本人权的首相。在我看来,如果有一个亚当•斯密主义,那么,它应当包含了生产生活与分配需求、市场机制与社会稳定、资本主义动因与社会主义价值三个层面的矛盾运动关系的表达。
基于此,亚当•斯密主义势必成为后来一切共和制民族国家的政府处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圭臬。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尽管经过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到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再到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一般均衡,经济学建立了一个抽象的理论体系,对人的假设也被简化成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此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日益完善,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尤其是那些系统性偏离了传统理性人假设所能预测的人类行为每当人们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切希望实现国家“良治”和人民休养生息的人们,特别是经济学家和政府首脑,都会回到他这里寻找走出困境的灵感和另辟蹊径的思想源泉。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或有志于经济学的人们,当好自为之!
2017年10月10日于复旦大学北区望道苑39号101A
注释:
1、参看《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的历史跃迁——论共生儒学》,2013年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雅典)参会论文。
2、上海企业史研究资深专家顾光青2010年6月9日报道:《人类经济学革命可能从中国开始——钱宏接受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并做学术报告》http://www.sass.org.cn/jjyjs/
3、“一次分配”(劳-资:生产性)、“二次分配”(政府-国民:福利性)、“三次分配”(公益,资产性投资-消费:货币扩展性)、“四次分配”(生产国-资本国:信用货币可印钞性)理论,还有“五次分配理论”,即“革命战争”推倒重来。——摘自《共生经济学•绪论》
4、参看钱宏:《中国:共生崛起》第177-20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5、参看钱宏:《五百年来谁著史,八万里路展风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2016.10
6、钱宏:《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历史文化观—理顺国家内部事务的两种实践方式与价值取向》注释,收录《原德:大国哲学》P274-28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11
7、参考《关于创设“环鄱阳湖生態文明试验区”的管见和建议》2008年2月25日给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函。我当时的设计,就是类似“基金操盘+生態引领”模式。